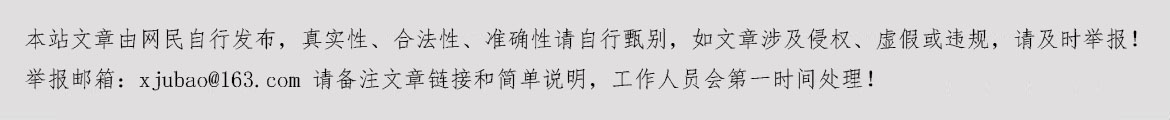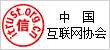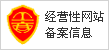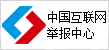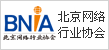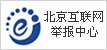1983年,我转业时很具戏剧性,还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儿……
2022-12-12 16:10:01
神奇的转业分配卧坡凡夫
1965年空军到我就读的眉山中学高六六级学生中“选飞”,谁也想不到的是,体重不足90斤的我在眉山初选合格,与其他合格的同学一起被送到乐山复检,竟然又过关了,最后与留下来的几名同学一起,送到成都去再次进行体检。一次比一次严格,一次比一次复杂,一次比一次让人受不了。在成都,我没有走完所有程序,中途就被淘汰下来,想飞上蓝天的梦想彻底破灭。也是这次“选飞”体检之路,让我这个农村娃第一次到了乐山,看到了乐山大佛,第一次到了成都,在锦江河畔的芙蓉餐厅吃了一次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也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回锅肉”!(这次“选飞”的结果是,只有高六六级一班的魏光明一个人被选上,但是到了飞行学院也没有完成学业,中途淘汰下来,去了成都七中继续读书。)
作者在青神408医院用这把圆锹种地
在“选飞”中没有能够穿上军装,却在三年以后的征兵时如愿以偿。
1968年,我高中毕业快两年了,由于那时候的特殊原因,我既没有升学,也没有工作,也没有回乡,也没有上课,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仍然在眉中晃荡,虚度时光。中途于六六年七八月间,被派往丁佑君的故乡——乐山五通桥的杨柳公社瓦窑大队搞了两个月“社教”,也叫“四清运动”。没有结束就被赶回了学校。回来后又无所事事,虚度时光。二十多岁的人了,还要爹妈供养,惭愧啊。
好在68年三月,国家发出了征兵命令。按照那时候的政治条件,我完全符合要求,所以报名应征。这可是我自作主张,没有告诉家人啊。因为我知道,凭我的身体条件,是不可能被选上的。哪个晓得在我的体重差两斤的情况下,接兵干部公然给与了特殊的优惠。(后来听接兵排长说,看在我是高中生的份上才被选上的——看来读书还是有用哈。)1968年3月18日我在三苏公园(现在的三苏祠)从头到脚都穿上了一身新军装。(硬是连裤带都没有留一根啊——原来穿的那身学生装都交给了爸爸带回家转给弟妹们穿。武装部还摆席三天免费招待军属,我爸爸和大妹妹到县城来送我,也享受了免费招待的。)脱去了学生气,换成了军人样,我从此吃上了军粮,每月还有几块钱的津贴,完全摆脱了依赖父母供养的困境,而且还能每月省下几块钱回馈父母了。我被选定为高原兵,知道比平原兵更辛苦,更危险,但是能摆脱那种浑浑噩噩的时光,我义无反顾,一路艰辛来到了西藏边防——拉康独立营步兵连三班。
记得刚到三班的第二天,班长陈丰元找我谈心,我就先问班长,你这四年是怎么过来的啊,他的回答很简单,说,这不一晃就过去了吗。(班长是1964年的兵,还是我们眉山老乡)。虽然天天都在喊“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但是那时候的西藏边防,确实条件太艰苦了。所以我一直想着把三年义务服满就退伍回家。一是可以离开艰苦边防,二是可以孝敬父母,三是可以早日完婚。
正如班长说的,“一晃”三年就到了,我满心欢喜地等到退伍。谁知道遇上了好领导,尤其是遇上了李政委,他就偏不让我退伍,只得服从,结果一干就是15年。详细情况在拙作《向李政委致敬》(见2022.8.23《今日头条》、《雪域老兵吧》)中做了叙述。直到1979年李政委转业回贵州贵阳农学院(他爱人所在单位),我送他到贡嘎机场(那时我已经调分区干部科工作),我们分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一批转业干部离开西藏时,干部科都要有人送他们到机场,送他们上飞机。临上飞机时,我紧紧地拉着李政委的手,半开玩笑半埋怨地说,李政委,你倒离开西藏咯,当年你不让我退伍,把我留下来,一干就是10多年了,还不知道好久能转业呢。这时李政委仍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邓干事啊,你要知道部队也需要人才,我们发现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人才也不容易啊。我们老了,干不动了。你要好好干啊,希望在你们身上啊!后来,我还是拒绝了几次升职的机会,终于于1983年转业了。
我和那把圆锹
说到转业,也很戏剧性的啊。我是属于山南分区1982年转业的那批干部,由于干部科人员紧张,这批转业干部工作还由我在内地具体负责落实,也就是除了安排其他20多名干部外,我还要自己安排自己的工作。按理说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哈。让人值得一笑的是,我只知道离我家比较近一点的属于国防工办系统的电子部部属的青神4501、863、867三个工厂,所以在我的转业去向里就填了上面的三个厂(后来这三个厂都先后破产了)。因为我们干部科原副科长刘廷富已转业到863厂任人事科长,我有一个表姐夫叫祝光华转业到4501厂任组织科长,想通过他们给我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并且已经收到了他们的建议。同时我也托过在眉山县委组织部工作的同学,答复是只能到我爱人工作的永寿公社安排工作,因为我怕看到他们中的一部分干部大碗转着喝酒,叶子烟(土烟)啪嗒啪嗒,讲话“出口成脏”的场面,所以放弃了回公社的想法。坚定了去国防三线单位的主意,想的是那些单位的人员素质要高些,当时流行的是“精兵强将上三线”的口号。我由于忙于落实其他干部的安排,认为自己的档案已经到了国防工办,工作已经基本落实,就没有过多的过问。结果我收到的转业干部任职通知是:电子工业部第408职工医院党委办公室秘书。真是“天山掉下个林妹妹”。408就408嘛,不给组织添麻烦,服从!后来才知道,位于青神黑龙场的“三厂一院”都是电子工业部(原机械工业部——四机部)的部属单位,都是县团级待遇,408医院就是原来四机部的第八所职工医院,还是属于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呢。而我到医院是不是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得了个天大的好处呢。(后来我那个副科长和那个表姐夫还因为没有去他们单位而有看法呢。)
说到转业,还有一件让我十分感动的事不能不说。因为我在内地安排与我同批转业的山南分区的干部,就没有再回部队去收拾自己的行李。我便委托了我们干部科的一名年轻干事(受他的嘱咐,隐去他的名字)帮我收拾。要知道,这可是个苦差事啊。而这位干事毫无怨言地接受这个委托,并且尽心尽力地,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个委托。给我用三个毛箱子(用厚木板钉起来的箱子)装完了我宿舍里的全部家当,连一把军用圆锹和两把铁制折叠架架办公椅都在里面(按理说这是公物,应该交公的),安全地送到了我的新单位。架架椅在四川潮湿气候下,几年就锈坏了。唯独这把圆锹陪伴我开荒、种地、养花,一晃就四十年了,跟随我转战西藏、青神、眉山,屡建功劳。我一直把它像宝贝一样带在身边,虽然被光阴磨去了一半,但是和我一样,一身沧桑,却仍然健在——生命在于运动的结果吧。我将把它留作永久的纪念。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这位干事的尽心尽力的责任心和真心实意的战友情。这位干事的工作能力和为人处世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部队官兵的重视和认可,官至西藏军区XXX军分区副政委,大校军衔,转业到成都后现已退休,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今年年初他又专程来眉山看我,还带来了我们两个在部队时的唯一一张合影老照片,促膝回顾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些事、那些人,让我再一次感动不已。
作者(左)和那位年轻干事
由于我安排这批转业干部工作到83年5月份才圆满完成,可以称得上我是属于站好了部队的最后一班岗啊。所以我的离队时间就成了83年5月,地方上从6月才给我发工资。也是这样,我在西藏海拔3500米以上地区工作就满了15年,办理退休时,就提高了10%的比列,结果我享受了百分之百的退休费。然而好景不长,在后来的调整工资中被慢慢地淡化掉了。不管怎么说,起码还是体会过一阵国家对曾经长期在高原地区工作过的人员的关心和照顾啊。(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笑话:在办理退休时,市人事局竟然有个年轻办事员提出,我那个证明是手写的,认为不正规,弄得我啼笑皆非。好在那个西藏山南军分区政治部的公章不是假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边防,分区机关也只有一个打字室,并且还是机械打字,好多的重要文件都要排队等待打印。——这么个证明根本就排不上队。——经过解释和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老局长认可后终于生效。)
报到那天,我和我爱人(我爱人随同从永寿中学调到408医院任教育干事)骑着自行车从永寿过了两道河(人工撑的木船),到张坎,再沿着眉青公路上山到了黑龙场的山上,沿路打听408医院,中午时分才到医院人事科李文良科长处报到,受到了他和黄伟院长的热情接待。但是又有一点小差错,就是可能电子厅发通知的时候,把医院办公室写成了党委办公室,经领导解释,我没有怨言,服从安排,到医院办公室当上了秘书。
医院领导很重视照顾转业干部的,给我分配了一套二楼28.88平米的大套间,第一次住上了楼房。现在看来房子好小,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带厨房、卫生间、前后阳台,自来水,天然气的房子,已经是够现代化的了,不再到公共厨房等候做饭了,不再去排队上公共厕所了,不再上公共洗澡堂几个人共用一个热水龙头了,家里虽然安的是院内电话,长途需要通过总机接转,但是还是可以叫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一家人可高兴了,我太满足了。要知道,我在部队时住的是土坯铁皮房啊,刮风下雨下冰雹都会打得铁皮生响,习惯了,就当作交响乐来欣赏了。爱人和两个小孩在永寿中学住的也是过去的寺庙隔成的不到10平方的木制青瓦房,唯一的好处是有一个40瓦的电灯泡,但是学校晚上10点就关灯了。
大概过了半年左右,我爱人到四川省电子厅参加职工教育工作会议,才从电子厅转业干部办公室徐素英处长那里得知我被分配到408医院的真正原因。
会议空余时间,徐处长得知我爱人是408医院的,就问她,今年转业到你们医院的邓泽斌怎么样,医院还满意吗?(徐处长不知道她问的人就是我爱人——这个世界有时候很大,大得不得了,有时候真的又很小,小得来面对面。)我爱人淡淡地说了一句还可以。这时徐处长却徐徐道来,深情地说,人家408医院的李文良可是为了要一个满意的秘书等了三年啊。当今年的转业干部档案到了电子厅后,我特别留意这个事情,看到邓泽斌的档案后,我首先就想到分配给408医院。408医院的李文良来接收转业干部分配人员时,我对他说,老李,今年我给你推荐一个,包你满意。李科长仔细地翻阅完我的档案后高兴地说:好,我们终于等到了。正好医院也需要一名教育干事,我爱人是中学教师,就给我爱人安排了教育干事职务。就这样我们被阴差阳错地分到了408医院。等徐处长说完这些后,我爱人才给徐处长挑明了我们是夫妻关系,弄得徐处长不知所以,说到我幸好没有说你们老邓的坏话啊,两人相视一笑。爱人开完会回来给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原来如此。
在几任院长长(黄伟、杨庆祚、罗会烈、刘世镶、陈念永、薛红)的正确领导和决策下,医院成功搬迁到了城市,我的工作也得到了肯定。从秘书到办公室主任、监察室主任、两办主任(党办、院办合署办公)、机关党支部书记,在医院从三线搬迁到眉山、眉山地区人民医院挂牌、眉山市人民市医院挂牌、与眉山县人民医院合并成为眉山市人民医院的过程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业余时间,还在《工人日报》、《健康报》、《人民卫士报》《乐山日报》《眉山日报》上发表了多篇宣传医院科研、改革、搬迁、医疗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好人好事的文章,让医院的声誉和影响力得到提升。总之,我没有辜负苦苦等候了三年的电子工业部第408职工医院的期望,心中感到十分的欣慰与人生的无悔。
作者发表的部分关于医院的文章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邓泽斌:笔名卧坡凡夫,东坡故里人,1947年出生,电子科大秘书专业毕业。1968年入伍,西藏边防服役15年,眉山市人民医院退休。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养花,偶尔动笔,无论文体。拙作散见于《半月谈》《健康报》《工人日报》《秘书》《厂长与秘书》《军工报》《晚霞报》《眉山日报》《在场》《今日头条》《青萃》《雪域老兵吧》《雪域情怀吧》等,还参与过几次各级机构的征文并获奖。
作者:邓泽斌